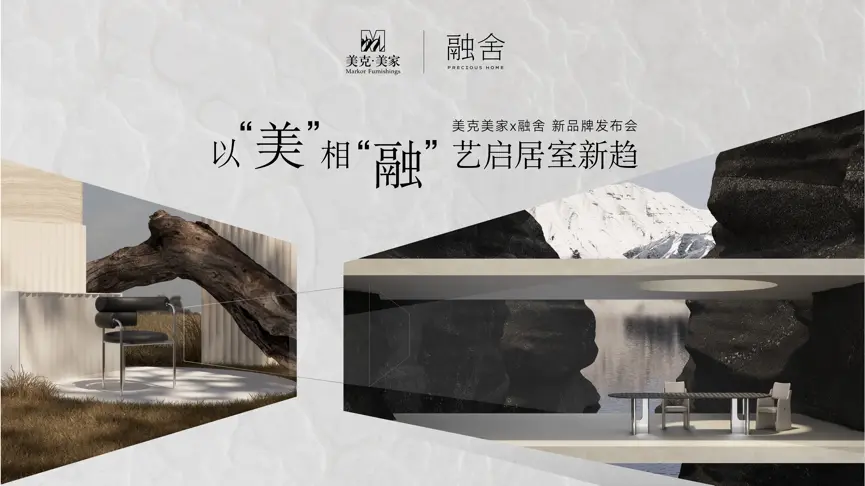早上10点,吴兴国背着双肩包,独自来到排练厅。
剧组工作人员极少看到他拿手机,“但到了约定时间,他一定准时出现”。吴兴国自言:演员把钟点刻在心里。
这次为京昆新歌剧《凯撒》首演,吴兴国留长了头发,“唱京剧要勒头,所以我一直剪小平头,有十多年没有那么长的发型了”。他把大背头抓乱,头发随意散下,“喷上发胶,就是古代罗马人”。

《青蛇》中的许仙等角色,让吴兴国为大众熟知。《封神》中的闻太师,则是他给观众的惊喜。40年来,吴兴国的名字更多地与先锋戏剧相连。没想到采访中,他随口唱起了京剧《白毛女》,说起传统戏时如数家珍。
功到自然成
吴兴国编剧、执导,与张军共同主演的《凯撒》年初在香港首演,4月底参加上海·静安现代戏剧谷后,6月将亮相台北,接着计划回到故事发生地意大利。“我想找一个真正的古罗马剧场演《凯撒》。”
事实上,早在2019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,《凯撒》已进行推介演出。“也许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创作。”吴兴国说。
上观新闻:《凯撒》是您创作的第6部改编自莎士比亚的跨文化剧场作品,它对您的吸引力在哪里?
吴兴国:香港艺术节找到我委约创作。我想做一些有文学性的剧目。我不太喜欢《奥赛罗》,他莫名其妙杀妻,脑子不够聪明,我不知道怎么搞剧本,于是想到《凯撒》。
我喜欢悲剧,演过《四郎探母》《打棍出箱》《捉放曹》《霸王别姬》,都是悲剧。西楚霸王到了乌江,明明可以遁走,免于一死,但他觉得逃亡很丢脸。凯撒也有点这种意思,他明知有危险,可以换一种选择,却还是义无反顾去了元老院。观众熟悉凯撒,适合舞台改编。我从传统戏曲出发,把莎士比亚的《凯撒》精简为两个演员集中讲故事。
上观新闻:您在《凯撒》中饰演贾修司、凯撒、安东尼,用了丑、净、生的表现方式,如何确定分工?
吴兴国:《凯撒》最主要的角色是贾修司与卜拓思,贾修司偷鸡摸狗,煽动卜拓思刺杀凯撒,我把他变成小丑。安东尼是大将军,用了大武生的演法,凯撒则是花脸。
我小时候学武生,后来学老生,在《李尔在此》中反串过各种行当。1994年我和梅派青衣魏海敏在法国演京剧《霸王别姬》,霸王是花脸。这次演凯撒,我也用花脸的范儿,有气势。我们穿的战甲效仿古罗马,我又加上了水袖、厚底靴,渗入了东方气质。
上观新闻:《凯撒》打出京昆新歌剧旗号,您如何看京剧、昆曲不同的特质以及合作演员张军?
吴兴国:京剧讲忠孝节义,昆曲偏重风花雪月。《凯撒》是400年前莎士比亚写的2000年前古罗马杀人事件,我们现在演,如何让观众代入?张军饰演2000年前的诗人,被误闯入古罗马遗址的现代青年唤醒。张军是预言者,还是整个故事的主角卜拓思。卜拓思像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周瑜,是年轻有为的将军,偏向文武小生。
上观新闻:观众看完后惊叹,《凯撒》与传统京昆剧目相比,音乐独树一帜。
吴兴国:《凯撒》作曲许舒亚教授把东方五音元素与西方古典音乐结合。创作之初,我有压力:我需要许舒亚的才华创意,又怕成品不合设想,就得吵架,要大改。拿到《凯撒》音乐小样,我一听,哎呀,好到不行,我很快乐。
演绎许舒亚的音乐,也难到不行。剧中,安东尼有一段宣言,我觉得太重要了,不能删。但许舒亚认为,安东尼唱到中途停下讲宣言,打破了旋律连贯性。我们各有坚持,你来我往地争论。最后他同意在间奏放两小节音乐,让安东尼把宣言讲完,但是他不给我完整的两小节八拍,而是三拍半、两拍半,非常没有规律。我每次唱前,都要背几十遍乐谱。
张军的段落也是这样,他饰演的卜拓思刺杀凯撒后,有一大段独白,每句重音都必须刚好卡到音乐结尾,极有挑战性。
上观新闻:张军有了新身份,他是演员,还是上戏附属戏曲学校校长。您也曾是大学戏剧教授,你们会讨论如何教学生吗?
吴兴国:我经常演出,把中国传统戏曲嫁接到西方经典文学。我舍不得放弃让观众起立鼓掌,因此没有像张军那样全职从事教学。我很佩服张军,老师为下一代作贡献,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。
我组建了年轻的团队——兴传奇青年剧场,已经成立8年了。4月底,唯一向我磕过头的徒弟朱柏澄参加湖北卫视的《戏码头》。他很紧张,那期《戏码头》压轴的是裴艳玲,参加者都是梅花奖得主。我让他演大陆难见的冷门戏《凤凰台》中的孙策,出奇制胜。
上观新闻:您对年轻演员传授的最重要心得是什么?
吴兴国:我和年轻团队一起跑圆场、练飞脚,一踢就是200腿。我不像年轻时候那样有劲了,但还是要做。传统戏曲,不管哪个剧种,体力都是第一。我小时候,老师一直强调,练功练功练功,功到自然成。没有体力,高音上不去,时间一长,嗓子就唱劈了。
50分钟《挑滑车》,演员扎上大靠,穿上厚底靴,排练时一连演三遍,否则上台一定会喘,怎么当主角?怎么打胜仗?传统戏的重头戏都在最后三分之一,将军得胜耍大刀、拧旋子,这也是演员最难的时候,太累了。我和学生讲,功力不够、体力不够,上台都是心惊胆战,做什么都不行。现在观众要求更严格,演员动作不稳,观众马上觉得不行,一竿子把那么难的综合艺术全打低分。
上观新闻:您如何保持良好状态,在71岁时自编自导,还上台演那么吃重的戏?
吴兴国:我的膝盖、腰都有伤,但坚持练习,就只是小发作。我50岁以后再没喝过汤,吃火锅也是涮涮清汤,偶尔补补钙片,简单就好。你要放纵享受生活,不控制欲望,就不能吃戏曲演员这口饭。假如太累了,我吃点维他命B,主要还是练功。
我们常说“返老还童”,人老了,智慧减弱,变得天真,身体也一样,越来越迟钝。要像小孩一样活泼,小孩不懂累,一直玩。像小孩一样把工作当作玩,我可以坚持很久。
戏曲榨干一个人的能量
12岁,吴兴国被送入“复兴剧校”坐科8年,因属于“兴字辈”而改名。成绩优异的他,后被保送到大学戏剧系。1986年,吴兴国和一群年轻演员创立“当代传奇剧场”。他们将传统京剧与西方经典结合,让传统和现代在剧场相遇。
上观新闻:当代传奇剧场是怎么来的?您当时是立志打造一个传奇吗?
吴兴国:20世纪80年代,看戏曲的都是老年人。我们一群大学生经常喝着咖啡,焦虑京剧的未来。戏曲剧团每年比赛,五六年里,我几乎每天都听到类似的话——不好好努力,不拿第一,剧团明年可能就解散。
经常来我家的年轻人想在传统基础上创新京剧。我们大概10个人,有一半是我的大学同学。我们取名“当代传奇剧场”,“剧场”可能性大,包容戏剧、音乐、舞蹈等表演形式,“当代”指当下,“传奇”重点在题材故事,一定是传统、经典的故事。文学史中有唐传奇等说法,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个传奇。
当代传奇剧场第一个作品是改编自莎士比亚《麦克白》的《欲望城国》。每位长辈都说,我们在瞎搞,但是《欲望城国》已经在排了,而且排了一年多,所以我想说:台上见。《欲望城国》首演结束,台下像烧开水一样沸腾了,全部年轻人抱在一起大哭。
上观新闻:现在回想早年当代传奇剧场的创作,您会想到哪个作品?
吴兴国:很多作品都有故事,比如1990年我演了《王子复仇记》,还不能叫《哈姆雷特》,因为只截取了莎士比亚原著中的一些片段,把很多角色都拿掉了。《哈姆雷特》十万字,我只演了其中不到两万字。我在大学读过很多莎士比亚戏剧,教授们特别在乎完整正确,所以我都不敢叫《哈姆雷特》。
中国戏曲与莎剧剧场有异曲同工之处,舞台是空的,强调虚拟性,三五步千山万水,六七人百万雄兵。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这类长篇小说变成京剧,也是一折一折戏,比如一小时的《林冲夜奔》,小说只有半页纸。京剧也可以演一晚上的全本《关公》,浓缩他人生几个重要片段。
上观新闻:您现在推出新作品,遇到的争议比年轻时少吗?
吴兴国:少太多了。1978年,我拜台湾京剧四大老生之一周正荣先生为师,他对我的创意从来没讲过一句话。我们当时需要演新编戏,光演传统戏,拿不到资金支持。我向周师父磕头以后接的第一个新编戏是《陆文龙》,内容、情节和老戏不太一样。我师父一看剧本就摔了,说:“我不演,你年轻,你去演。”
离首演只剩两个月,我连夜把所有我认为可以用的唱腔反复听,然后开始消化,攒字韵、身段,上下句不能编错了。从《陆文龙》开始,我编了《淝水之战》《孔雀胆》《孙膑与庞涓》《通济桥》《屈原》《袁崇焕》。还好有新戏的经验,否则我成立当代传奇剧场,肯定撑不过5年。
上观新闻:您提到传统戏的概率,比我预想的要高得多。
吴兴国:中国传统戏曲的可能性太多了,能把一个人的能量都榨干。比如《打棍出箱》描摹主人公的疯狂状态,动作一次次重复,推动情感走向高潮。30多年前,我师父演《打棍出箱》给蒋勋看,他非常感动。《打棍出箱》剧本凝练,4个片段不拖泥带水,不是写实地演疯子,过程又这么悲哀,不断重复,好到不行。我后来做《等待果陀》,用了《打棍出箱》中的一些技巧,贝克特的剧作通过戏曲形式变得有了独特性。
上观新闻:2006年,莫言看完您演的《李尔在此》后写下《柏林观戏》,“在柏林世界文化宫大剧场舞台上,吴兴国一人分饰十角,生、旦、净、丑,唱腔形体频转换,给观众留下思索的巨大空间”。在柏林,您有难忘的故事吗?
吴兴国:2006年柏林艺术节做中国文化月,我演《李尔在此》。艺术节安排我去中学做讲座。一进教室,我傻眼了:50多个学生,有人抽烟,有人化浓妆。我也不多说,直接飞脚、虎跳、翻跟头,把学生的眼睛和耳朵拉过来,接着教他们学动作。小孩们立刻兴致勃勃,一小时讲座后,还有人递手帕让我擦汗。我走时,他们站两排欢送,与来时完全变了样。戏曲基本功实在太难了,有些段落堪比特技,拿十分之一去国外,都能让观众震惊不已。
上观新闻:您在大学时还是云门舞集骨干,堪称多栖演员。
吴兴国:林怀民老师根据京剧做了很多舞蹈作品,比如《白蛇传》《奇冤报》。《奇冤报》我有个动作,向后退,直挺挺倒下去,像戏曲“僵尸摔”,不到十分钟,要摔两次。舞团训练辛苦,皮破,膝盖痛,有人喊累。我学戏曲出身,从来不怕累。
云门舞集在美国三个月巡演,我们像鸽子一样,坐六七个小时大巴,下车进剧场排练、演出,演完后在小旅馆睡一觉,接着去下一个地方。我演《奇冤报》连摔三个月都没事,就这样摔,被“摔”出来了。
从许仙到闻太师
电影《封神》第一部片尾彩蛋,吴兴国饰演的闻仲露面,激起观众回忆。《青蛇》许仙、《诱僧》石彦生、《宋家皇朝》蒋介石、《赌神》仇笑痴、《长恨歌》李主任……大家纷纷留言,列举吴兴国的经典角色。影视剧带给吴兴国支持剧团发展的资金,还有迥异于舞台的表演体验。
上观新闻:乌尔善导演看了您的《欲望城国》,邀请您演《封神》,这是戏剧感挺强的电影。
吴兴国:我到现在还没有时间看《封神》。我大概去了剧组三次,每次拍十天左右。闻仲在第一部坐着巨大的墨麒麟出现。实际拍摄时,我坐在形似马鞍的椅子上,有两三层楼高那么高,腿上稍微绑了一下,要做出骑麒麟摇晃的样子。这又要感谢戏曲训练,京剧骑马,连坐垫都不需要,一根马鞭足矣。我给闻太师穿了厚底靴,这样比较有劲儿。最难忘是给闻太师做面具,本来说两个小时,结果做了四个小时,我差点晕过去。
上观新闻:您因为《诱僧》石彦生一角获得金像奖最佳新人奖,听说这部戏一开始定的不是您。
吴兴国:我对石彦生很有想法,付出也很多。他是大将军,我先在北京学了两周骑马,才去平遥拍。武生演员学跑马很容易,罗卓瑶导演看我骑得很棒,加了追杀戏,我领兵沿着平遥高墙策马转弯冲向镜头。
拍完后,她又加了一场,还是石彦生领着这些人策马回家,告诉母亲赶紧逃。第一条拍得很顺,挑担的群众演员看到马冲过来时往旁边闪。再拍一条,出事了,群演回头看我的马近了,没有逃走,反而蹲下来。马已经停不住,我只能狠拉缰绳,让马跳起来,群演毫发无伤。马“咚”的一下,把我甩出去了。
当我从医院醒来时已经过了三小时。导演哇的就哭了。X光拍到我头上有两个大口子,幸好只是固定头盔的发夹,没有真扎进脑袋。
我的脸还肿着,演我妈妈的卢燕进剧组了,她是长辈,不能耽误时间。我用网纱贴在脸上遮伤,然后化妆。和卢燕的母子拜别戏,只拍侧脸,我偶尔转头,也不能幅度太大。
上观新闻:您在云门舞集《白蛇传》演了无数次许仙,这些经验有没有用在电影《青蛇》上?
吴兴国:徐克找我演许仙,是他在利舞台看过我跳的《白蛇传》。拍《青蛇》时,我反复提醒自己——我不会武功、不会踢腿,我是只会四书五经的游医,拍摄的两个半月基本不练功。
《青蛇》里河上放灯、楼上教书,在上海车墩拍了一周。游湖借伞在香港海边一个叫“三杯酒”的地方,剧组非常小心,不拍到周围的山。雨水用海水喷,像消防队一样。徐克要求机轮船不开发动机,一群工作人员下海慢慢推船,营造浪漫效果。
徐克拍电影可厉害了。演员签约每天拍12个小时,徐克总在超时。他在片场摆着躺椅,休息20分钟起来,对接下来拍什么一清二楚。白蛇的家是两层半铁皮屋,场务布置灯光,开圆窗,种竹林。床也很简单,全靠烟、风、灯光做效果。他从躺椅上醒来后开始指点。他说话很快,一分钟说完,这里不行,那里不行,全组人“啪啪啪”改置景,动作快到不行。徐克就开始指导演员,比如张曼玉在地上像蛇一样爬行,他会先做示范。
上观新闻:《青蛇》很神奇,首映至今31年,吸引了一代代观众,不断有新的解读。
吴兴国:十多年前,我在福建拍电影《爱在廊桥》。灯光助理来自北京电影学院,他告诉我:“好佩服你的许仙,《青蛇》太棒了,是北京电影学院研究所学生必修的功课。”
《青蛇》有个场景要镜头旋转起来,从演员上方往下拍。徐克拿一根绳子把摄像机吊起来,架梯子,爬上去算好镜头范围和距离,然后开拍。他一直用最简单的方式拍最难的镜头。
我说:“你真厉害,怎么想到这样用机器,摄影师都做不到。”徐克说:“我读书时,每天扛机器到处拍,然后剪啊、弄啊,都是自己来。”我后来才知道,他在纽约街头拍片,扛了三年机器。
《青蛇》首映发布会前,我们还在赶拍法海抓到许仙,飞到金山寺修炼。徐克在破屋子里,把我和赵文卓吊起来拍,一旁电风扇呼呼吹,营造衣服的飘动感。徐克的美术概念很棒,他觉得氛围不够,拿了纸在上面画,然后用剪刀修,做成云朵。灯光一打,喷烟雾,“云朵”看上去更有层次感。结果首映会看片,全场哄堂大笑——这场戏赶时间,又是光影摇曳,后期制作没有把吊演员的钢丝完全“擦”干净。
上观新闻:听说徐克每次拍戏都会先画一组画,让剧组所有人知道今天拍什么。
吴兴国:每天早上,演员化妆间外立着水牌,徐克像做漫画一样,一格格画好分镜头画面。他给我排舞台剧《暴风雨》也是这样,画大裙子,按照这个创意做服装。《暴风雨》根据莎士比亚的同名剧作改编,角色们遭遇暴风雨漂到岛上,男主角设置丰盛的宴会给大家吃。徐克在策划聊天时一直在想,然后就开始画了,连盘子里装的鹅和羊头都画得很清晰。需要什么样的“菜”和餐具,道具师一目了然。
上观新闻:您在采访中提到,在韩国演《暴风雨》,第一天就摔伤了胳膊,我很好奇,后续怎么样了?
吴兴国:叶锦添为我饰演的魔法师设计巨大的服装,底下装着近两米的钢架,工作人员躲在里面推着我走。韩国演出第一天,钢架四个轮子中的一个卡住了。工作人员用力一推,站在上面的我失去平衡,往下倒,用左臂扛住身体,就受伤了。当时还有一个小时的戏,徐克马上冲到后台,把我的袍子剪了一块作为吊绳拴住受伤的胳膊,我继续上场。万幸《暴风雨》没有大动作。演完后看医生,我的左臂骨头有两道裂缝。
有个同行教了我秘方,这次我也分享给张军:十个鸡蛋,只留蛋黄,混上等量盐巴,涂抹在伤处,然后固定胳膊。我继续演了两天《暴风雨》,动的时候胳膊痛,不过更有悲剧感了,观众看着很感动。
韩国受伤不到三个星期,我又演《陆文龙》耍双枪。演出中有一个高难度抛空背接,因为胳膊问题,我在台上坚持试四次才接到枪,观众一直喊加油。我就是这样任性,非成功不可。
上观新闻:拍影视剧、跳舞、唱戏,哪样最辛苦?
吴兴国:戏曲演员出身的人,拍电影不辛苦,包括云门舞集,也没那么辛苦。唱戏最辛苦,从小苦出来,15岁时,我在剧校练翻跟头,磕到头,昏过去。校医用自己熬的膏药给我糊一糊,好几个同学把我抬回寝室。中午,我醒来了,守着我的同学吓坏了:我明明知道他是谁,就是想不起名字。半年后,我又开始练翻跟头。一直到今天,唱戏、创作新戏,给我的满足感最大。
吴兴国
原名吴国秋,当代传奇剧场创始人兼艺术总监,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教授。在舞台创作中,融编导演一体,作品包括戏剧《欲望城国》《李尔在此》《等待果陀》《蜕变》《凯撒》以及电影《诱僧》《青蛇》《宋家皇朝》《封神》等。